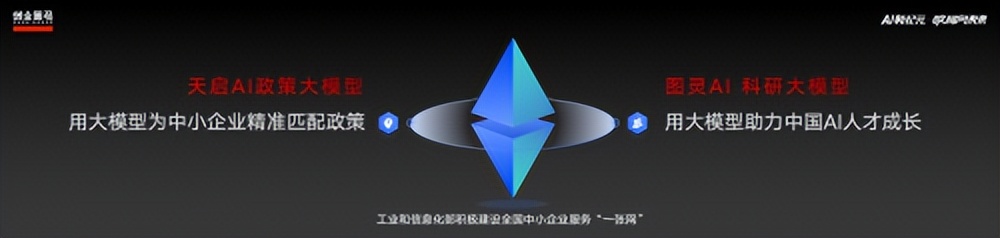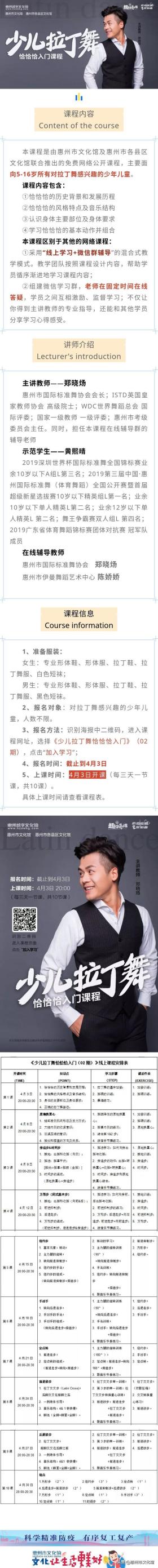我,张德明,1963年农历二月初二生于清水乡西山村。村里的老人们常说,二月二龙抬头,出生在这一天的人,长大后能救死扶伤,造福一方。或许正是这句话影响了我,从小我就立志要当一名医生。
我的家在群山环抱的小山村,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。为了让我读完医学院,他们省吃俭用,甚至卖掉了家里唯一值钱的一头老黄牛。这份恩情,我至今铭记在心,总觉得欠了父母太多。
1987年,我从省医学院毕业。当时,我的同学们都挤破头想去县医院工作,而我,却选择回到了家乡的清水乡中心医院。这个决定让我的同学们都笑话我是个傻子,说我这叫“高射炮打蚊子”。但我知道,清水乡周边十几个村子,就这么一个小医院,每天从四面八方赶来看病的乡亲们,让我看到了家乡对医生的渴望。
清水乡中心医院其实是一栋两层的土砖房。一楼是门诊和急诊,二楼是住院部,总共也就十来张床位。医院的院长老韩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中医,据说他年轻时在县医院当过十年院长,退休后不愿意闲着,就回到家乡办了这个小医院。
记得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,老韩拍着我的肩膀说:“德明啊,你能回来,可真是咱们清水乡的福气啊!现在年轻人都往外跑,你却往回走,这份心意,老头子我记下了!”
说起来,要不是那次去东山村卫生所送药,我可能就不会遇到陈雪梅了。那是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,老韩让我骑着他的永久牌自行车,给东山村卫生所送一批青霉素。东山村比我们西山村还要偏僻,山路崎岖,我骑着自行车,走走停停,差点迷了路。就在我手足无措的时候,远处传来一阵清脆的铃声,一个骑着凤凰牌自行车的姑娘从拐弯处出现了。
那姑娘穿着一件白大褂,戴着一顶草帽,帽檐上还沾着雨水。她停下车,问我:“同志,你是不是清水医院的?我看你好像迷路了。”我一看她胸前的工作证,上面写着“东山村卫生所 陈雪梅”,顿时喜出望外:“是啊是啊,我是来送青霉素的。”“那正好,跟我来吧。”她说着,就在前面带路。她骑得不快,好像是专门在等我。山路泥泞,她还不时回头提醒我:“这里有个坑,小心点。”就这样,我认识了陈雪梅。
后来我才知道,她是东山村卫生所唯一的一名医生,年纪比我大两岁,医术很好,在周围几个村子里都很有名气。村民们都亲切地叫她“陈医生”,说她医术好,脾气好,从来不计较个把钱,穷人家看不起病,她还倒贴钱给买药。
那天送完药,她留我喝了碗姜汤。我看到卫生所的墙上贴满了村民们送的锦旗,有一面锦旗上写着“医者仁心暖人心,女神医术济苍生”。陈雪梅不好意思地说:“都是乡亲们太客气了。”
从那以后,我就总想找借口去东山村。有时候是送药,有时候是请教医术,反正就是想方设法地往那边跑。老韩看出来了,常常打趣我:“德明啊,又去东山村啊?那边的陈医生,医术是不错。”说着,还冲我挤眼睛。
每次去,都能看到陈雪梅在忙碌。她给老人量血压,给孩子打针,给孕妇把脉,动作麻利,说话轻声细语。有时候我去得早,还能看到她在院子里的小菜园里侍弄几棵蔬菜。她说,这是留给住院病人吃的,买不起营养品,总得想办法补充点营养。
慢慢地,我发现自己已经记住了她的一举一动。她喜欢把头发扎成马尾辫,喜欢穿浅蓝色的布鞋,喜欢在口袋里放一支圆珠笔。她总是随身带着一个印着“上海”字样的旧挎包,里面装满了各种常用药。她说,这是她爸爸留给她的唯一遗物。
原来,陈雪梅的父母都是医生,在她十八岁那年,一场车祸夺去了他们的生命。从此,她就一个人生活。村里人都说她可怜,常常有人给她说媒,可她都婉言谢绝了。她说,自己要专心照顾乡亲们的身体,没时间想别的。
那年的秋天特别的冷。十月底的一个晚上,我正在值夜班,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打开门一看,是东山村的张大伯,他气喘吁吁地说:“德明医生,不好了,陈医生出事了!”
原来,当天晚上有个产妇要生孩子,陈雪梅骑着摩托车去出诊,回来的路上遇到了大雨,山路湿滑,摩托车打滑摔倒了。张大伯正好路过,这才发现昏迷在路边的陈雪梅。我二话没说,跟着张大伯就往事故地点赶。雨还在下,山路泥泞难行。我们用手电筒照着路,终于在一个转弯处找到了陈雪梅。她躺在路边,白大褂上沾满了泥土,右腿有明显的骨折,额头上还有一道伤口在流血。
“雪梅!雪梅!”我喊着她的名字,心都要跳出来了。好在她还有意识,微微睁开眼睛。我赶紧和张大伯一起把她送回医院。那一夜,我给她处理伤口、固定骨折,忙到天亮。老韩闻讯赶来,看了看陈雪梅的伤势,说:“骨折得不轻,得住院观察一段时间。”就这样,陈雪梅住进了我们医院的二楼。我主动请缨负责照顾她,每天给她换药、按摩。她开始有些不好意思,说:“德明,你别这么麻烦,我自己可以的。”我笑着说:“你别动,听医生的话。再说了,你平时帮了那么多人,现在该让别人帮帮你了。”
东山村的卫生所没了医生,我就主动跑去帮她代班。每天早上给她换完药,就骑着自行车去东山村,晚上回来还要给她做复健。那段时间,我忙得像个陀螺,可心里却美滋滋的。
有一天换药的时候,我无意中发现她枕头下压着一本日记本。她睡着了,日记本翻开的那一页写着:“德明真是个好人,这些天受了他那么多照顾。其实我知道,他经常偷偷地看我,以为我没发现。那天他给我削苹果,削了半天都削不好,手都划破了也不说。这个傻小子。”看到这里,我的心跳得更厉害了。原来,她早就发现了我的心思。我轻轻地合上日记本,放回原处,心里却像灌了蜜一样甜。
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,陈雪梅的伤也慢慢好了。她能下地走路的那天,我特意煮了一锅红豆粥给她。她喝完,突然说:“德明,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不找对象吗?”我愣住了,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她红着脸继续说:“我在等一个人,等一个像我爸爸那样,愿意扎根在农村,真心实意为乡亲们看病的好医生。这些天,我总算等到了。”说完,她低下头,声音越来越小:“德明,我。我嫁你。”那一刻,我的眼睛湿润了。窗外,夕阳的余晖洒在病房的地上,映出两个依偎的身影。
就在这时,楼下传来一阵喧哗声。原来是县医院的人来了,说要提拔我去县医院工作。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,我一时不知所措。县医院的条件当然比乡村医院好得多,可是……我看着陈雪梅,她的眼里闪着泪光,却努力挤出一丝笑容:“去吧,那是你的机会。”我摇摇头,握住她的手:“不,我哪儿也不去。我爸说过,二月二出生的人要造福一方,我就要留在这里,和你一起照顾乡亲们。”
听到我这么说,陈雪梅扑进我的怀里,哭得像个孩子。她说,这些年,她一个人在东山村的日子并不好过。有时候半夜三更要去出诊,路上漆黑一片,她就哼着歌给自己壮胆;有时候看到贫困的乡亲们付不起医药费,她就默默地从自己的工资里贴补;有时候累得实在走不动了,她就躲在卫生所的角落里偷偷掉眼泪。现在好了,她终于不用一个人扛了。我紧紧地抱着她,轻声说:“以后我们一起,我骑车,你在后座上看风景。”
第二天,老韩知道我拒绝了县医院的工作,却没有批评我。他笑呵呵地说:“德明啊,你做得对。这年头,谁都往大城市跑,可咱们山里的乡亲们,也需要好医生啊!”就这样,我和陈雪梅的故事在清水乡传开了。乡亲们说,这是天造地设的一对,都夸我们是“医界鸳鸯”。每天早上,我们一起骑车去各自的诊所,路过的村民们都笑着跟我们打招呼。
日子平淡却幸福。春天,我们一起给卫生所的小园子种上蔬菜;夏天,我们轮流去各个村里为老人们体检;秋天,我们一起去山上采药;冬天,我们踏着雪给偏远山区的孩子们送药。记得有一次,我们去最偏远的山村出诊,天黑得早,山路难走。陈雪梅挽着我的胳膊,轻声说:“德明,你说我们这辈子就这样在山里给人看病,值得吗?”我想了想,说:“值得啊!你看那些得了病的乡亲,见到我们就像见到了亲人一样。我们虽然赚不了多少钱,可是我们赚到了他们的信任和感激,这比什么都值得。”她点点头,依偎在我肩上:“是啊,我爸妈生前也常说,当医生不是为了赚钱,而是为了救人。”
日子就这样过着,我和陈雪梅的感情越来越深。我们商量着要把两个村的卫生所联合起来,打造一个更好的医疗站,让山里的乡亲们看病更方便。可是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,就在我们准备结婚的时候,一个意外的消息打破了平静。原来,陈雪梅的远房亲戚从上海来了,说要接她去大城市工作,还说已经给她在上海的一家大医院安排好了工作。这一次,轮到我患得患失了。我知道,这对陈雪梅来说是个难得的机会。上海的医院条件好,工资高,而且她可以接触到最先进的医疗技术。可是我又舍不得她走,舍不得这些年来朝夕相处的点点滴滴。
那天晚上,我们坐在医院的屋顶上看星星。陈雪梅突然说:“德明,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吗?”我点点头:“记得,那天下着雨,你骑着凤凰牌自行车出现在山路上,就像从天而降的仙女。”她笑了:“傻瓜,我那时候就觉得你不一样。别的年轻医生都往外跑,你却愿意回来,这份情怀,打动了我的心。”说着,她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,打开一看,是她爸爸留给她的那个“上海”挎包。